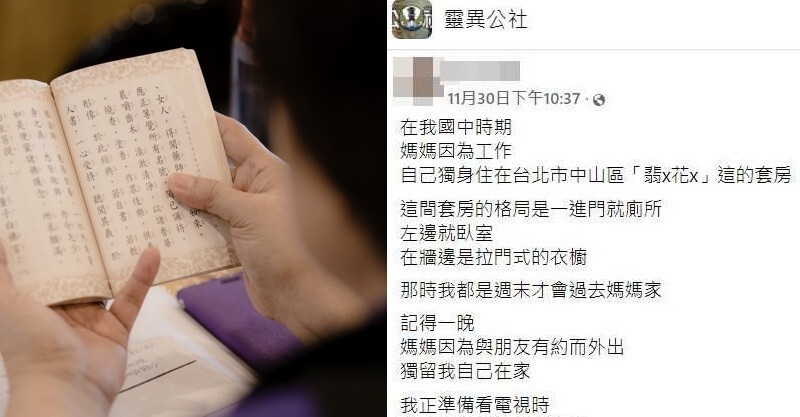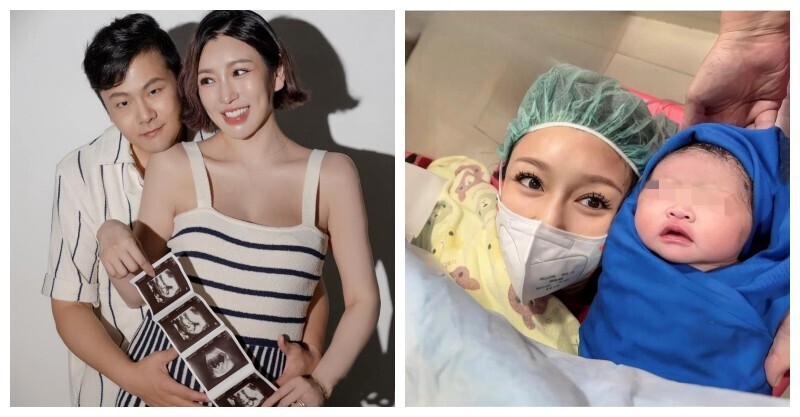10年前買下鄰居老宅!突傳敲門聲「竟是他想借屋辦喪事」 剛拒絕「媽媽開口痛罵我」讓我羞愧不已
冷漠門楣前的和解
「你啊,就是活該被人戳脊梁骨!連老祖宗的臉都給丟盡了!」母親的聲音在院子裡回蕩,鄰居們紛紛探出頭來。
我抬頭望了一眼母親,只見她氣得臉都紫了,手裡那把半舊的蒲扇抖個不停。
我叫周家明,今年四十有二,是這條衚衕裡少有的「成功人士」。
早年在縣城國營建材廠當會計,趕上了九十年代初廠子改制,靠著手腳勤快和一點小聰明,硬是在別人都下崗回家「吃西北風」的時候,搖身一變成了廠裡的銷售科長。
「公家的人」變成了「公司的人」,一個月固定工資變成了底薪加提成,我這日子一下子就紅火起來了。
單位分了一套六十多平的樓房,在城西新區,水泥外牆的筒子樓,沒電梯,倒是有獨立衛生間,不用再半夜提著馬桶去公共廁所倒了。
可母親就是不願意搬,她嫌那邊「人生地不熟」,說是老了,禁不起折騰,其實是捨不得這一片老鄰居。
Advertisements
她在這四合院裡住了大半輩子,認得每一塊磚每一片瓦,離不開這些「街坊四鄰的溫熱」。
十年前,我憑著在建材廠積攢的一點錢,加上銀行貸款,買下了隔壁王大爺的老宅子。
那是一處帶天井的四合院偏房,雖然破舊,土牆上爬滿了青苔,木門框都有些歪了,但在縣城這片老城區,地段卻是極好的。
「三年建材做下的家業,不如一年炒房賺的多」,這是當時廠裡跑業務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。
見房價慢慢往上漲,我也手癢了,想著弄套房子囤著,等過幾年拆遷改造,那可就是一棵搖錢樹啊!
王大爺膝下有子有女,卻在妻子病重時忍痛賣了祖宅。
那年他家辦紅白喜事可熱鬧了,兒子結婚,鑼鼓喧天,一脖子汗珠子,笑得見牙不見眼;媳婦進門,四合院的硬木板床上鋪著大紅的綢緞被面,綉著龍鳳呈祥。
Advertisements

沒想到不到三年,王嬸子就病倒了,一開始還硬撐著,說是「老毛病又犯了」,可沒多久連街口賣饃的老趙家都知道她得了癌症。
我從銀行貸了款,給了王大爺32萬,買下了這處本來他要價40萬的老宅。
Advertisements
那時我只當是個投資,心想過幾年城市改造,這地方肯定能翻幾番。
買下後我便鎖了院門,每月打掃一次,平日裡人影也不見一個。
那沉重的銅鎖掛在紅漆剝落的木門上,在風裡發出「咯吱咯吱」的聲響,彷彿在訴說著什麼。
王大爺一家搬到了城東的筒子樓裡,我們的來往也就淡了。
偶爾在街上碰面,他那雙渾濁的眼睛裡總透著說不出的複雜。
一次,我在百貨大樓門口遇見他買了半斤瓜子,手裡還提著個黑色塑料袋,裡頭鼓鼓囊囊的應是剛配的藥。
我知道,在他心裡,那老宅承載了太多記憶,可生活哪有那麼多選擇?
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,轉眼十年。
這些年我也算是混出了點名堂,從建材廠跳出來自己做生意,開了兩家建材超市,還在城南新區買了套一百三十平的商品房。
Advertisements
家裡添了彩電、冰箱、洗衣機,這些年輕時候想都不敢想的東西,如今都成了尋常物件。
連我那輛捷達都換成了桑塔納2000,停在單位門口,引得同事們一陣羨慕。
日子過得順風順水,王大爺家的老宅子卻成了我心頭的一個小疙瘩。
每次媽媽催我去打掃,我總是找借口推脫:「忙著呢,等周末吧。」
周末又說:「天太熱,改天吧。」
就這樣,那老宅子漸漸在我心裡變得遙遠,就像是一件塵封的舊物,不捨得扔,又嫌它佔地方。
昨日清晨,王大爺拄著拐杖來敲我家門。
他瘦了,臉上的褶子更深了,手上的青筋突起,像是老樹榦上盤錯的根。

Advertisements
「家明啊,」他聲音有些顫抖,「你王嬸子走了,家裡太小,辦不了喪事。」
他頓了頓,彷彿在積攢力氣,「能不能借用一下老宅子?就三天...」
母親站在廚房門口,手裡握著切了一半的青椒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我。
我猶豫了一下,心裡盤算著:老宅子早就沒人住了,灰塵厚厚的,裡面還堆了些雜物,哪能用來辦喪事?
再說了,死了人的地方,晦氣啊!
萬一以後想賣,還得跟買家說明情況,可不是砸自己的飯碗嗎?
我當即搖頭:「王大爺,那房子空了好些年,又髒又破,哪能用啊?」
「再說了,死人的事,晦氣...」
「你住嘴!」
母親的喝斥聲如同一道閃電劈開了早晨的寧靜。
轉頭一看,母親站在門口,臉上怒氣沖沖,眼中的失望如刀子般刺來。
我從來沒見過她這副模樣,平日裡她最疼我,就算我做錯了事,她也總是護著。
Advertisements
「當年你發高燒,是王大爺半夜背著你去醫院的!」
母親的聲音裡帶著從未有過的嚴厲,「那會兒可沒現在這麼方便,路燈壞了一半,連個計程車都叫不到。」
「你爹出差,我一個人慌了神,是王大爺在醫院守了一宿!」
「你小子有出息了,就翻臉不認人了?」
母親的話如同一盆冷水,澆在我心頭。
記憶如潮水般湧來——兒時在王家吃的餃子,那香噴噴的豬肉白菜餡,是王嬸子親手剁的;和王大爺兒子小林一起爬樹掏鳥窩的日子,掉進池塘后被王大爺揪著耳朵罵了一頓,卻又給我們烤乾了衣服;還有那年我考上縣高中,王嬸子包的肉粽子...
這些片段在腦海中閃回,像是一部泛黃的老電影在放映。
「家明,」母親的語氣忽然軟了下來,夾雜著一絲嘆息,「老王家賣房子那會,王嬸子已經查出肝癌晚期了。」
Advertisements
「他們賣房子是為了治病啊。」
我心頭一震,手腳頓時變得冰涼。
十年了,我只記得那是筆劃算的買賣,卻忘了背後的故事。

當年,這套院子原本王家要價40萬,我硬生生砍到了32萬,還暗自得意自己會談生意。
沒想到,那兩萬塊錢的差價,對他們而言可能意味著多一次化療的機會,多一線生的希望。
我突然覺得喉嚨發緊,說不出話來。
那冬日裡王大爺搬家的背影,扛著一床棉被,滿頭白髮在風中飄動的情景,忽然變得無比清晰。
當時他是不是也是這樣低聲下氣,求著我給個合適的價錢?
「老王頭一輩子要面子的人,能來求你,得有多難啊!」母親的聲音拉回了我的思緒。